再论共同危险行为——以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
内容提要: 现代侵权法的数人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理论基础从“主观说”转化为“关联共同说”,对共同危险行为的体系定位产生了重大影响。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不再是共同过失,而是客观危险的可责难性。共同危险行为侵权责任构成的因果关系应采“群体危险行为”理论。共同危险行为人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并按照客观危险比例进行最终责任分担。证明自己没有实际造成损害的共同危险行为人,应该对其他连带责任人承担补充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10条规定:“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文对共同危险行为侵权责任的规定,补充了《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该类型数人侵权行为的遗漏,意义重大。“共同危险行为”这一术语源于日本民法判例学说,在德国法上被称为“参与危险行为”。[1]43我国侵权法上的共同危险行为,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实施有侵害他人权利的危险的行为,对造成的损害结果不能判明谁是加害人的情况。[2]从实务角度看,共同危险行为案例的绝对数量是较小的,但从研究的角度则颇具理论价值。共同危险行为既是《侵权责任法》起草过程中的重大争议问题,也是《侵权责任法》未来实施中的疑难问题。本文特别从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新定位的角度,对共同危险行为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重点探讨。
一、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理论对共同危险行为体系定位的影响
(一)共同侵权行为“主观说”理论框架下的共同危险行为体系定位
在共同侵权行为“主观说”理论框架下,共同危险行为因为欠缺意思联络,[3]166而不同于共同侵权行为,但也因缺乏主观共谋而面临受害人无法求偿的风险。立法者从保护受害人的法律政策出发,拟制所谓“共同过失”和“选择性因果关系”,由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以致害性行为关系与致害人是否明确为分类标准可以将主观说下数人侵权行为交互分类如下表:
|
行为关系/致害人是否明确 |
致害人明确 |
致害人不明 |
|
|
共同故意 |
(1)共同侵权行为 |
(2)共同侵权行为 |
|
|
共同过失 |
(3)共同侵权行为 |
(4)共同危险行为 |
|
|
无主观共同 |
数个独立行为 |
数个独立侵权行为 |
致害人不明单独侵权行为 |
|
客观共同行为 |
|||
从上表可以看出,“主观说”强调承担连带责任必须有共同过错,(1)表明典型的共同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是共同故意;(2)表明致害人不明的共同故意数人侵权也是共同侵权行为;(3)表示部分学者认为的共同过失可以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前提是致害人明确,经典的案例如郑玉波先生所举的“负重登高案”;[4]143(4)表明对共同危险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基础的解释则依托于共同过失,认为“参与这种具有危险行为的本身,就表明他们具有疏于注意的过失”。[2]由于传统民法基于过错责任原则对共同危险行为采“共同过失说”,只能够解释主观上具有共同过失的危险活动致害问题,但无法对主观上无共同过失的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的共同危险行为进行界定。
(二)共同侵权行为“关联共同说”理论框架下共同危险行为体系定位的变化
《侵权责任法》第8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由于没有规定主观共同过错要件,实际上采纳的是“关联共同学说”。所谓“关联共同”,包括“主观关联共同”与“客观关联共同”两类,将原本无法由共同过失解释严格责任共同侵权行为,纳入到下图(5)客观关联共同的解释范围内。值得指出的是,在共同侵权行为理论从“主观说”扩展到“关联共同说”的过程中,学说上并未显示出对共同危险行为体系定位的考虑。[1]因采纳“关联共同说”的实际体系效果是,由于主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范围扩张到了全部的共同过失领域,使得上表(4)所示依托于共同过失的传统意义上的共同危险行为被实质性的纳入到了主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领域;同时共同危险行为范围实质上扩展到了(6)不具有主观关联共同而具有客观关联共同的致害人不明数人侵权行为中,其体系变化的结果如下:
|
致害性行为关系/致害人是否明确 |
致害人明确 |
数人中具体致害人不明 |
|
|
主观关联共同关系 |
主观故意关联共同 |
(1)共同侵权行为 |
(2)共同侵权行为 |
|
主观过失关联共同 |
(3)共同侵权行为 |
(4)共同侵权行为 |
|
|
客观关联共同关系 |
(5)共同侵权行为 |
(6)共同危险行为 |
|
|
无关联共同关系 |
数个单独侵权行为 |
致害人不明单独侵权行为 |
|
从上表可知,共同危险行为的理论基础已经由共同过失理论转化为客观关联共同,在体系上随着共同侵权行为的扩大而产生了“位移”。即无主观关联共同的数人共同参与实施具有致害他人危险的行为且已造成实际损害,而具体的加害人不明时,由于该数人并不存在主观关联共同,无法将他们的行为加以一体化处理认定为共同侵权行为,如果存在客观关联共同,则以共同危险行为制度加以处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4条将其表述为“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不能确定实际侵害行为人的”,使用了“共同”的字样,是较为准确的。
(三)共同危险行为在数人侵权行为理论体系中定位变化的理论基础
这种定位上的变化,实际上是理论体系发展的必然推论。史尚宽先生在分析共同危险行为时,认为行驶于同一道路的汽车,其中一车伤人,不能认定为共同危险行为,但如果两车是超速竞赛就是共同危险行为,“盖两车俱已关与竞赛之危险行为也”。[5]176梅仲协先生也认为,“数人共同发生侵害他人之事实,而不能知其孰为加害之人者,亦应负连带责任(危险责任主义)”。[6]198邱聪智先生也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人并非确为加害人,其负损害赔偿责任,系法律拟制所致,无意思联络的情形也可能适用共同危险行为规则。[7]123孙森焱先生更是明确指出,数人所谓的行为,虽未能具体的辩明孰为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但具有侵害权利的危险性,故共同危险行为的共同关联性即为数人共同不法的行为。[8]233
我国民法学界有也学说认为,“有共同违法行为或者共同危险行为,即具有客观上的关联共同”。[9]923《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4条的规定更加突出“危险”概念,即“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这也印证了笔者所持的责任基础是危险而非主观过错的观点。
某种意义上说,在主观说下的共同危险行为,尽管以保护受害人受偿为目的,苛加危险行为人连带责任,在客观关联共同说被承认之前,相对于共同侵权行为的主观共同要求,过于向受害人一方倾斜。在承认了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之后,共同侵权行为与共同危险行为在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上保持了一致,反而显得更加公平了。
(四)共同危险行为的侵权责任构成基础是客观危险的可责难性
实施了共同危险行为,直接根据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似乎存在没有规定侵权责任构成,直接规定侵权责任分担的假象。事实上,这正揭示了共同危险行为理论本身,也必须对侵权责任构成进行说明。笔者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中的“危险”不但具有客观的危险性,而且是一种应该而且可以避免的危险,因此具有较强的可责难性。根据形成危险就应当承担危险的规则,每个共同危险行为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危险,故共同危险行为人应当对其危险行为负责。[10]750无论是实际致害人,还是其他未造成损害的共同危险参与人,均是在为其参与共同危险行为,而非为其实际造成损害承担责任。[11]103-110这是基于危险行为本身的可责难性而承担的民事责任,即“行为的危险性是致人损坏的原因”。[12]340在共同危险行为中,不是因为实际致害,而是因为参与危险行为具有较强的可责难性,而承担连带责任。
二、客观关联共同说下的共同危险行为侵权责任构成的因果关系结构
(一)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两种因果关系理论
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因果关系,德国法有所谓的“选择性因果关系”理论,[13]449传统美国法上也有类似的“选择责任”(alternative liability)理论。[14]119-124王泽鉴教授持该学说,[1]44我国学者也大多赞成,并认为共同危险行为本身是一种因果关系的推定,[10]742适用举证责任倒置。[10]74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7项也规定:“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不过,因为“共同危险行为人中,不能知其中孰为加害人,严格言之其中有行为对损害并无相当因果关系”,[5]173所以对“选择因果关系”理论也不乏反对意见。如孙森焱教授指出,因为其责任之成立要件应系每一可能之肇因者,其行为被视为是损害之原因,因之须为侵权行为或危险负责。假如结果只能由加害人之一引起,却去推定每个人均系肇事者,本非合理。[8]233黄立教授也指出,这一认定无论视为举证责任转换或以危险责任观点来看,均非合理,除非参与人间由共同行为之意识,才由承担连带责任之合理根据。因此德国学说对此规定颇有批评。[15]302
应该认识到,“选择因果关系”理论的问题,主要是基于其主观说的定位而导致的。除了上述反对理由,笔者还两点反对意见:第一,如果按照选择性因果关系推定共同危险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共同危险行为人应该承担的就不是连带责任,而应该是不真正连带责任,但这显然不是选择性因果关系理论试图得出的结论。第二,具有危险性的共同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客观的因果关系,[16]602因此共同危险活动与损害的因果关系无需推定。问题的关键不是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因果关系的证明问题。[1]43-44
比较法上,除了德国法的“选择性因果关系”理论之外,法国法发展出了“群体危险行为”理论。由于《法国民法典》未对致害人不明数人侵权行为的责任规则作出明文规定,上个世纪50年代法国法院在面临“打猎案”时,为了避免受害人无法获得救济的情况出现,提出了将责任基础从行为直接导致损害(the conduct which immediately led to the injury)移转到某个行为可以被归咎于(imputed)实际致害人必然是其中一人的群体上。是整个群体(the whole group)通过其(its)[2]过失行为产生了危险,原告的损害是危险的现实化(realization)。作为这种理论的必然推论,该群体中的每个人都被认为是有责任的,因此承担连带责任。该理论还被适用于一群小孩参加危险活动和年轻人参加暴力活动的案件中。[17]443如1968年,法国最高法院要求袭击了一童子军营地的“青年帮”的成员证明他没有扔石头造成损害。此后,“每一个参与危险活动的人对危险活动可能造成的全部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很快成为在不能判断谁实际上造成了损害之情形的责任确定标准。[18]85-86尽管该理论仍然是一种因果关系的推定,但在因果关系的结构上,通过“群体危险行为”的构造,将因果关系的推定限制在参加该危险行为的程度,却避免了直接推定每个共同危险行为人直接导致损害的理论困境,似乎更为合理。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法学会《侵权法重述·第三次·财产和精神损害责任编》第28条第b款规定:“当原告起诉数个行为人并证明每个行为人都参与了导致原告面临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危险的侵权性活动,以及一个或者多个行为人的侵权性活动导致了原告的损害,但原告无法合理的被期待那个证明实际导致损害的行为人,包括举证责任和说明责任在内的对于事实因果关系的证明负担被移转给了被告。”该条文官方评论第g条特别说明:“所有导致原告面临损害危险的被告的侵权性行为被连结成了选择责任的前提”,[3]这实际上改变了美国侵权法上选择责任因果关系理论类似德国法“选择性因果关系”的传统模式,而更接近法国法的“群体危险行为”因果关系。
(二)客观关联共同定位下共同危险行为应采“群体危险行为”因果关系
笔者认为,法国法的“群体危险行为”理论与“客观关联共同说”的理论框架更为契合。共同危险行为人是一个整体,不可分离。[16]603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解释共同危险行为的责任也只有一个责任,不是由若干分责任组成,而是不可分割的完整责任这一法律现象。[16]607共同危险行为无需再借助所谓拟制的“选择性因果关系”,也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推定问题,而应该适用“关联共同因果关系”,即将符合客观关联共同的共同危险行为人视为整体,其行为结合成危险活动,其关联共同性表现为参与危险活动,因果关系存在于作为整体的危险活动与损害之间,是危险活动而非单个的危险行为造成了损害。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尽管没有明确采关联共同说,但在官方说明中也认为,是“整个共同危险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关联性。”[20]72 “群体危险行为”主要由行为的危险性与群体性两方面构成。
行为的危险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行为具有致害的可能。Markesinis教授指出,共同危险行为自身并非不法,但必须有对他人的潜在危险性。[21]900数人实施的行为有致人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这种致害他人的可能性可以从行为本身、周围环境以及行为人对致害可能性的控制条件上加以判断;此外,这一行为没有人为的侵害方向,共同危险性不针对任何特定的人。[16]602行为致害的可能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以“打水漂案”为例,所谓时间维度,即行为致害的结果必须在行为之后,如在受害人已经被击中之后,才参与打水漂;所谓空间维度,即行为致害的范围在空间上具有有限性,某一行为人为6岁小孩,力气太小不可能击中行为人。
第二,行为的同类致害性。危险行为并非必须是同类行为,但必须具有同类致害性,这种危险性的性质和指向是相同的。[20]71危险行为的同类性还表现在均具有违法性上,在德国法上,如果其中一个参与人的行为是合法的(例如有权使用武器),则不但排除了他个人的责任,同时受害人也不能根据第830条第1款第2句对其他参与人行使请求权。[22]238-239
第三,危险的不合理性。共同危险行为中的“危险行为”与高度危险行为致害中的“危险行为”含义显然是不同的。高度危险行为致害的“危险”是即使尽到高度注意义务,采取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造成损害,但由于科学技术和其他方面的限制,不可能完全预防可能发生的危险,[16]485-486而共同危险行为中的危险,是只要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就可以预防发生的一般危险,只是由于行为人的过失或者行为不当,导致这种本不应该面临的社会危险出现并造成损害,这种危险性是不正当、不合理的。[23]708同时危险性具有较强的法律政策因素影响,如在闹市区高楼上向下扔玻璃瓶,具有对社会的极大危险性,尽管玻璃瓶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是特别危险,但人人皆知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应该认为有较强的危险性和可责难性。
判断行为是否具有群体性,即危险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客观关联共同性而构成危险活动,应该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危险行为之间具有时空一致性。一般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不以主观上彼此知悉和从事集体行为为必要,[1]46-48但致害性行为应有“一定空间与时间上关联”,[15]300尽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同时同地,但此仅为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史尚宽先生认为:“数人需关与有为侵权行为之危险之行为(因其发展可导入直接引起损害之行为)”[5]175并举例,同宿舍二人,其中一人因过失酿成火灾,另一人虽“同宿一室,不能谓其已关与危险行为。”[5]176王泽鉴教授也认为“此应就造成危害的时空关联加以判断”,同时也举例认为“森林因有人丢弃烟蒂引起火灾,不能认定当日登山的人,都是共同危险行为人”。[24]216
第二,危险行为人具有参与人的性质。主张共同危险行为者,应积极证明被告有所行为,始得请求连带赔偿损害。若无加害行为,则不得主张共同危险行为。[8]233在危险行为具有群体性的判断标准上,则具体化为危险行为人是否具有“参与人”的性质。所谓“参与人”,即如果只需设想某人的行为确实导致了损害的发生,则他就能满足了包括过错的在内的、侵权行为的全部构成要件,那么他就具有了参与人的性质。也就是说,对于实现侵权的构成要件来说,只有对加害人是否造成了损害这一问题,允许存在情况不明的状态。受害人对损害的存在、侵权行为参与人的过错、违法性,原则上仍然要承担举证责任,只是对于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需负举证责任。[22]235
三、共同危险行为的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选择
(一)比较法上的多数意见是连带责任——以“打猎案”为例
比较法上对于共同危险行为的共同关注源于早期各国普遍出现的“打猎案”,案情大致相似:多位猎人对第三人方向开枪,其中一位猎人的子弹击中受害人,但不知具体是谁的子弹击中。德国最高法院早在1909年就作出了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4]法国法上确立连带责任的案例是1957年的Litzinger v. Kintzler[5]一案,并将这一做法延续下来,多次作出判决。[25]3641970年《西班牙狩猎法》规定:如果一个人在狩猎中被击中又不能认定是谁击中的,所有的狩猎参与者被认为负有连带责任。该规定于1983年通过判决类推适用到一起普通民事案件中:一群在公共道路上玩耍并扔小金属片的儿童,受伤的人未能指认谁扔的金属片扎伤了他,最高法院判决所有的儿童的父母承担连带责任。[18]84奥地利、希腊、荷兰和意大利等国尽管没有类似案件发生但也持类似的态度。[25]388日本上未见“打猎案”,但有类似的“抛石案”:“各人行为均有致他人的伤害的危险,为保护受害人,理应由抛石人共同负责”。[26]112
英国法院没有作出过关于“打猎案”的判决,[17]444英联邦法院在这方面的例案是加拿大最高法院1951年判决的Cook v. Lewis[6]一案。对于类似案件如果在英国法院进行判决的可能结果,尽管有少数英国学者认为可能面临和因果关系基本原则的冲突,[27]p223更为主流的意见则持肯定的态度。[28]252早期美国法上法院对“打猎案”一般根据证据法上的“更可能有”(more likely than not)规则来确定责任,如果D1打出了两颗子弹而D2只打出了一颗,那么D1承担全部责任,而D2不承担责任。在Summers v. Tice[7]一案中,加州最高法院面临了新的困难,由于两个加害人都只打出了一颗子弹,因此各自仅有的50%加害可能无法达到“优势证据规则”(preponderance evidence)的50%以上的要求,受害人可能因此无法向任何人请求损害赔偿,因此创造性的判决二人承担连带责任。[29]226-227可见,作为典型的共同危险行为案型的“打猎案”,在比较法上均适用连带责任。
(二)新近出现的按份责任形态理论及其理论困境
一般认为,在具体的加害人不能确定的时候,侵权法面临是否所有的参与者都要承担连带责任,抑或如果原告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他们可以逃脱责任两种选择。[18]81不过近年来也出现了新的按份责任形态理论,笔者仅对两种具有代表性理论进行评论。
1.Spier教授的“自己责任论”。在《欧洲侵权法原则》中,因果关系部分起草者Spier教授特别强调其基本观点是责任人仅对其造成的损害负责,即不对他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损害部分负责,不论该部分是他人、受害人或者自然原因造成的。[30]46因此由其起草第3:103条“选择性原因”第1款规定:“在存在多个行为,其中每一行为单独地都足以引起损害,但不能清楚确定事实上是哪一个引起了损害时,可根据每个行为引起受害人损害的相应范围的可能性认定其为受害人损害的原因。”更规定实际上是按照风险大小比例适用按份责任,[30]48并且明确排除第9:101条第1款第b项“一人独立的行为或活动引起受害人的损害,而同一损害也可归因于另一人”的连带责任适用。[30]144甚至还认为在可能由人为原因或者自然原因造成的损害案件中适用,如在登山者可能被其他登山者导致的或者自然滚下的落石击中的案件中,认为受害人可以向他人请求一半的损害赔偿。[30]57作出这种按份责任规定的理由是,一方面没有强制性的理由让责任人对他可能并未造成的全部损害负责,另一方面也不能让受害人不能得到赔偿。[30]48在笔者看来,Spier教授的“自己责任论”至少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而不可取:1、在逻辑方法上,Spier教授选择按份责任的理由,简而言之,就是不能承担连带责任,也不能不承担责任,因此只能承担按份责任。但在笔者看来,依照其不能为他人承担责任的一贯逻辑,即使按份责任也不应该承担。因为承担按份责任的基础,应该是加害人造成了该部分损害,现在受害人无法证明谁是加害人,并不等于加害人按照其致害比例造成了部分损害,也不能承担按份责任。可见,通过仅探讨不能承担连带责任和不承担责任的排除法来论证承担按份责任的正当性。也是不合理的。2、在逻辑论证上,存在理论上的自身矛盾。Spier教授自己也承认,可能出现部分共同危险行为人无法查明的情况,因此无法按照其设计的按份责任进行分担的问题,并提出由法院忽略无法查明的共同危险行为人,针对能够查明的被告进行按份分担的思路。[30]49这种选择显然与其自身理论矛盾,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既然按份责任的基础是不能为他人承担责任,而这种妥协方案实际上就是在为不能查明的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责任。第二,如果只有一个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查明,实际上仍然是连带责任,这恰恰是该理论试图否认的。第三,如果承认可能的加害人为可能的自然原因负责,如“登山案”,则在很大程度上撼动了因果关系的基本理论,也与其自己责任理论矛盾。
2.Epstein教授的“受偿风险概率论”。美国的Epstein教授则另辟蹊径,从受害人完全受偿的概率和受偿程度的角度对按份责任的思路进行了论证:假设D1和D2两个共同危险行为人,D1没有赔偿能力,D2有赔偿能力,二人造成损害的概率各为50%。如果最终查明损害是有D1造成的,则受害人P无法受偿,因为D1没有赔偿能力;如果是D2造成的,则P可以完全受偿。因此按照案件可能的情况,P有50%的可能性全部受偿,这种结果与苛加D1和D2各自50%的按份责任的效果是相同的。[29]227Epstein教授的论证看似合理,其实却存在逻辑上的错误。在查明加害人的案例中,P要么受偿,要么不受偿;但在共同危险行为中,正是由于无法查明加害人。这好比天气预报的降雨概率,如果说明日降雨概率50%,同时也是在说明日的不降雨概率是50%,但明日是否降雨只有一种情况,即降雨或者不降雨。概率统计不能直接决定单独事件的发生,这是概率论与决定论的根本差别。因此,这种论证方式只能用于较大数量的同类侵权行为,如后文将要提到的市场份额理论,但不能用于共同危险行为的个案。
(三)我国《侵权责任法》上共同危险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正当性
关于共同危险行为侵权责任形态的选择,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保护受害人”不应成为连带责任选择的唯一理由。《德国民法典》第830条第1款第2句的立法目的在于使受害人摆脱举证困难的困境,即在多人参与的侵权行为案件中,当无法完全准确的确定真正的加害人本人时,受害人的请求权不能因此无法实现。[22]234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说继受了德国法的“保护受害人”学说,认为“其规范目的在于处理因果关系难以认定的困境”,[24]216其意旨无非为保护受害人而设。[7]123我国侵权法学说和司法实务,[20]71也大多持“受害人保护说”,认为免除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而对其提供优厚保护。[9]923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构成与侵权责任分担,不应该受到致害人不明这一案情的影响。因此“保护受害人”的立法目的,既不能使本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的行为人承担责任,也不应该使本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的责任人承担连带责任,只是促使我们通过法律技术,绕开致害人不明这一证据障碍,根据其他案情认定侵权责任构成和确定侵权责任分担的标准。
第二,共同危险行为是数人侵权行为形态问题,而不是侵权行为类型问题,因此需要作出选择的是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因此不存在不真正连带或者补充责任的适用问题。在其他基于共同的危险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类型,如产品责任、数人环境侵权责任和数个雇主共同导致的雇员因接触石棉而导致间皮瘤的案件中,可以根据法律规定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共同危险行为可能存在于同类或者不同类的各种侵权行为类型中,是关于数个侵权行为之间的关系描绘,因此应该适用侵权责任分担论中关于一般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即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的选择理论。[31]
第三,由于共同危险行为的致害人不明特征,使得按份责任的适用其实是不可能的。其理由在于,可能的致害人要么导致了损害,要么没有导致损害,不存在可能导致损害的问题,按份责任的承担,是在为“虚无”的“可能责任”负责。而连带责任的制度价值之一就在于,由于受害人可以向数个连带责任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请求全部的损害赔偿,因此实际上免除了受害人确定被告之外的其他加害人的负担。如果共同危险行为人的数个被告本来就构成了连带责任,那么就可以通过连带责任制度本身的特点绕开致害人不明的问题。因此,起诉共同危险行为人的请求权基础,是在于共同危险行为人本来就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其是否就是实际致害人,则是共同危险行为人内部的问题。
综上所述,客观关联共同定位下共同危险行为的侵权责任形态问题,需要与共同危险行为侵权责任的成立同时判断。其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不是主观的共同过失,而是客观共同危险群体行为具有较强的可责难性。共同危险行为成立,则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危险行为不成立,则不承担责任,因此不存在按份责任的适用可能。因此,《侵权责任法》第10条坚持规定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立法选择是十分明智的。
(四)共同危险行为人之间的最终责任分担规则
《侵权责任法》第14条第1款规定:“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但我国民法学者一般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人的责任份额,原则上应该平均分配。[32]198主要理由是,共同危险行为人在实施共同危险行为中,致人损害的概率相等、过失相当,各人以相等份额对损害结果负责,是公正合理的。[16]620但在例外情况下,也可允许斟酌具体案情,参照危险行为的可能性的大小按其比例分担。[10]751在笔者看来,“原则”与“通常”代表了法律的不同态度。尽管“通常”情况下,共同危险行为人的责任划分上,一般是平均分担的,[16]606但从“原则”上看,共同危险行为人分担最终责任的基础应该是客观危险。如果行为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几率并不相同时,则应当依据几率的大小确定原因力的大小,进而在共同危险行为人内部分配赔偿责任的份额。[33]404因此,《侵权责任法》第14条第1款的规定也应该适用于共同危险行为。如A、B、C三人为某品种烈犬爱好者,A有两只,B、C各一只,大小类似,因爱好相同而聚在一起放逐相互攀比。D因有急事奔跑而过,四只狗一同追逐并有其中一只狗将D咬伤,从伤口上无法确认是哪只狗咬伤,则应由A、B、C三人承担连带责任,并按照2:1:1的比例进行内部分担。
四、共同危险行为人免责事由的“补充说”
关于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实际造成损害,是否能够作为免责事由,学说上一直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
所谓“肯定说”,即认为,法律规定共同危险行为制度的目的,使在无法查证情形下,消除受害人举证困难的问题,而不在为其找寻更多的债务人。其他参与人可以通过证据证明,其行为或者协力,绝无可能导致损害之发生,而免除责任。[15]301比较法上,美国法认为作为一种举证责任倒置规则,[8]持肯定说。[9]法国法上认为这种因果关系是推定的,可以由被告证明其未造成损害。[17]443德国法则认为,被告与损害之间必须具有最低限度的潜在因果关系,因此可以通过证明其不可能造成损害而免除责任。[17]445我国传统民法学说上,梅仲协先生持肯定说,[6]198史尚宽先生则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人不独证明其未加损害,而且须证明其未为损害之条件或原因,始得免其责任,[5]176该说是对肯定说的进一步发展和精细化。张新宝教授指出,与肯定说相应的,是不能免责的其他共同危险行为人之间,继续承担连带责任的结论。[34]88《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4条采肯定说,也有学者指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7项的规定:“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民事诉讼证据也采肯定说。[33]405
“否定说”认为,若仅证明自己无加害行为,而不能证明孰为加害人者,既无法确定责任之归属,自仍应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35]61郑玉波教授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5条第1款后段规定的“不能知其中孰为加害人者,亦同。”立法语境下,精辟的指出:“盖法文明定‘不知’孰为加害人即应连带负责,因而虽能证明其非加害人,但仍不能因之即‘知’孰为加害人,故仍不能免责”[4]144我国大陆法学界,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持否定说,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人不因证明自己的行为造成实际损害而免除连带补充责任,还必须要证明谁是真正的行为人。[36]
《侵权责任法》第10条改变了传统民法的立法思路,先规定“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再规定“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这种立法模式实质上回避了对“肯定说”和“否定说”的选择问题,但在《侵权责任法》未来实施中这一问题必须得到回答,尤其是部分危险行为实施人可以证明自己不是实际致害人的情形。笔者认为,由于共同危险行为的要件不是很严格,因此其法律效果也是缓和的。[37]763对于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未实际致害是否能够作为免责事由,应该从追偿权的行使角度来考量。共同危险行为的最终责任应该由实际加害人来承担,如果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实际加害人,即能够排除最终责任的适用。如无特别理由,不承担最终责任的责任人,出于追偿程序行使方便和效率的考虑,应该赋予其顺位利益,即由其他不能证明自己没有造成损害的责任人先行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无法完全受偿时,才由其承担补充责任。鉴于此,笔者建议未来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采纳“补充说”,借鉴我国侵权法上的补充责任制度,[38]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实际加害人的,免除其承担连带责任,但若受害人无法从其他连带责任人处完全受偿的,由免除连带责任的加害人承担补充责任。这种制度设计相对于受害人并无改变,但免除了非实际致害人的连带责任,进一步缩小了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更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行为人的自由。
本文标签:四川自考 法学类 再论共同危险行为——以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
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http://www.sczk.sc.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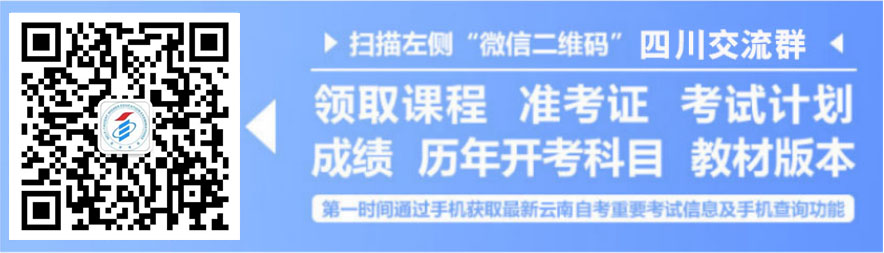
《四川自考网》免责声明:
(一)由于考试政策等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本网站所提供的考试信息仅供参考,请以省考试院及院校官方发布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
(二)本站文章内容信息来源出处标注为其他平台的稿件均为转载稿,免费转载出于非商业性学习目的,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您对内容、版权等问题存在异议请与本站联系,我们会及时进行处理解决。联系邮箱:81237948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