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内容提要: 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一、问题的提出
依王泽鉴所言,合同履行请求权之要件,至少应包括如下两项:(一)合同成立;(二)合同生效。[1]42实务中,若案件事实充分各项构成要件,则应赋予其法效果。但诉讼中,主张该项请求权者,应否证明生效要件之存在?这关涉证明责任的分配。因为,在司法三段论的逻辑演绎中,证明责任问题存在于法官演绎推理的小前提之中,其适用于对拟判决案件事实的真实性审核。[2]8
就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5条第1款前句(该条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规定,主张履行请求权者(原告)(当然,证明责任的分配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原告或被告)无关。但主张履行请求权者,除消极确认之诉(有时还包括消极形成之诉)外,均为原告。并且,“在司法实践和学术研究中,人们频繁使用‘原告的证明责任’或者‘被告的证明责任’术语,这是可以谅解的”。(参见本文参考文献[4],第260页。)所以,本文为求表述简便,径以原告代称主张履行请求权者。另外,基于合同关系而提起诉讼者,不仅限于履行请求权,尚包括其他请求权。但请求履行是所有这些基于合同关系之诉求的典型内容,因而,本文仅以履行请求权为例,论述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应承担合同生效要件的证明责任。但李浩撰文指出,原告不承担双方都具有行为能力的证明责任。[3]565如果对该文结论稍作推论,应可得出原告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也不承担证明责任。因而,依李浩之论,原告不承担“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李浩立论前提为“成立、有效、生效”之“三分说”,关于此点,详见下文。)。那么,《证据规定》第5条的规定是否妥当?
现代证明责任理论认为,证明责任是实体法中的一种风险分配形式,证明责任的分配概由实体法规定。[4]29既然如此,我们可基于解释论的立场,探究《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并以之检讨《证据规定》第5条的妥当性,为其寻求解释论上的适用方案。学者多以为,合同效力要件有别于肩负私法自治重任的成立要件,它体现国家管制的意旨,[5]169那么,效力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在法技术构成上应如何调和国家管制与私法自治之间的失衡问题?由此,本文的写作即是以此为个例,分析实体法中的证明责任规则,探讨民法解释论的实践价值。
二、合同特别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的基本功能在于,将诉讼中各个案件事实真伪不明导致的败诉风险分配给双方当事人,并以此保证法院裁判义务在事实真伪不明时,仍能实现。[4]33学说上多认为,《证据规定》第2条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与“规范说”相一致(对此种共识,可参见翁晓斌:《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现代法学》2003年第4期,第74页;张卫平:《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规范说认为,此种败诉风险分配,根源于实体法的具体规定。而实体法上的具体规定,具言之,指的是实体法规范之间的相互对立或排斥的关系。但这并不是指规范之间相互矛盾,而是法规范中,既有权利据以产生之基础规范,又有阻止权利产生或使已产生的权利归于消灭的相对规范。[2]105基础规范,也称权利产生规范。相对规范可分为权利阻碍规范和权利消灭规范,前者是指阻碍某种权利产生的规范,后者是指使已经产生的权利归于消灭的规范。基于这三种类型的规范,“规范说”提出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为,“每一方当事人均必须主张和证明对自己有利的法规范(=法律效力对自己有利的法规范)的条件”。[2]104也就是,主张权利者,仅需证明权利产生规范之要件事实;抗辩之被告,则应承担权利阻碍规范或权利消灭规范之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
就合同履行请求权而言,所谓权利消灭规范,主要指的是《合同法》第91条之规定。该条规定,合同权利终止的原因(该条款规定: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包括: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解除、债务相互抵消、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债权人免除债务、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证据规定》第5条第1款后句及第2款对此有规定,被告应对这些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合同生效要件,不属于权利消灭规范之要件,至为明显。依《证据规定》第5条第1款前句,主张履行请求权者,须证明合同生效要件,即《证据规定》将合同生效要件认作权利产生规范之要件。那么,该条规定之“生效要件”具体为何?
李浩认为“具有行为能力”属于有效要件,不属于《证据规定》第5条之生效要件,其所谓生效要件仅指附条件合同之停止条件、附期限合同之始期以及特殊合同的批准、登记手续。[3]556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李浩此论(生效与有效不同)源自学说上“成立、有效、生效”之“三分说”。但令人疑惑的是,论者还将有效要件进一步区分为一般有效要件与特别有效要件,并且其所谓特别有效要件指涉的也是停止条件、始期以及批准、登记手续。[3]554-555依其理路,特别有效要件与生效要件是同义语。那么,有效要件与生效要件岂不是没有区别?李浩前后所论,岂不矛盾?或许,为避免在概念上缠夹不清,论者退而认为,“从民事诉讼的角度,还是能够把‘生效’和‘有效’作适当区分的”。[3]556但证明责任属实体法内容,无由从诉讼的角度探究实体法之制度构成。或许,论者所言证明责任指的是诉讼中的主观证明责任?但主观证明责任的标的及范围,与实体法上的客观证明责任相一致并由后者决定(此处所指主观证明责任仅限于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因为主观具体的证明责任“取决于法官的证明评价,而不是依赖于证明责任规范”。(本文参考文献[4],第43页。)所以,对这种非规范性的主观具体证明责任的探讨,毋庸讳言,在此处是多余的。)。也就是说,已由实体法规定之生效要件或(和?)有效要件的(客观)证明责任分配,决定诉讼中主观证明责任分配。就此点,根本不可能从诉讼角度(主观证明责任)区分实体法中的生效与有效。论者所言,倒果为因,立论前提难以成立,不足采信。由此,其结论也有“毒树之果”的嫌疑。
就该问题,本文径依通说之观点,采“成立、生效”之“二分说”(关于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多放在法律行为章节中讨论,对此问题可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以下;梁慧星:《民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68页;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以下页;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以下。),生效与有效并无实质区别,合同有效要件仅是生效要件的另一称谓而已。[6]390此种“举重若轻”的简单处理,原因在于,本文采解释论立场探究合同效力要件之证明责任,其论证自当以实在法规定为基点,此外,还受制于由制度化推动的法学所阐释的教义学。[7]20此种教义学,表现为各个理论通说。虽然以教义学切断论证之无限递归,无疑也属于“明希豪森困境”[8]39之一种,但本文认为以通说为起点的法律论证,更有利于接续法学知识传统,而免于自说自话或概念语词的无谓论争。依通说,合同生效要件可分为一般生效要件与特别生效要件。《证据规定》第5条所称“生效要件”,涵括二者,还是仅指其一,不得而知。对此二者,以下分述之。
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之特别生效要件,包括附条件合同之停止条件(《合同法》第45条)、附期限合同之始期(《合同法》第46条)、特殊合同的批准、登记手续(《合同法》第44条第2款)。依“规范说”的规范分类方式,该三条从积极方面(基于此种特性,陈自强将之称作积极的有效要件,参见本文参考文献[9],第351页。)(自……时生效)规定合同权利应该产生的条件,均应属于权利产生规范。因而,此三项特别生效要件,属于权利产生规范的要件,应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规定之特别生效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也遵从了通说之观点,即特别生效要件原则上与合同成立要件相同,应由主张履行请求权之原告承担证明责任。[9]352如对于附条件合同,原告应就停止条件的成就承担证明责任,被告应证明解除条件的成就,学说上已无异议(但须注意的是条件成就之证明责任,与条件约定与否之证明责任不同。对后者,不论其为停止条件或解除条件都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对此,可参见本文参考文献[2],第285页;骆永家:《民事举证责任论》(第5版),台湾商务印馆1987年版,第174页。)。[10]373另外,对于附期限合同,因为“条件在内容上通常也是附有期限的法律行为,在停止条件上乃附有始期之行为”。(然而在“期限”所探求的是“何时到来”,而在条件所探求的则为“是否到来”的问题。参见本文参考文献[10],第367页。)因此,始期届至与停止条件成就之证明责任分配,适用的规则一致,仍应由原告证明。再如,合同批准、登记手续之证明责任分配,则应类推要式合同对“合同形式”之证明责任。所谓合同形式,乃是合同意思得以示之于外的方式,[11]3对合同合意的证明,即包含着对合同形式的证明。所以,合同批准、登记手续之具备,也应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
三、合同一般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以证明
责任为法解释目标
(一)效力阻却要件与一般生效要件之扦格
与特别生效要件不同的是,《合同法》并未从积极方面规定一般生效要件,而是从消极方面(无效、可变更可撤销、效力待定)列举规定“欠缺一般生效要件”的三种情形,分别为合同无效(第52条)、可变更可撤销(第54条)、效力待定(第47、48、49、50、51条)。依“规范说”的分类方式,它们均属于权利阻碍规范。本文将其要件,称作“效力阻却要件”(苏永钦根据法律对特别生效要件与一般生效要件的规定模式,分别将之称为积极的生效要件与消极的生效要件。参见本文参考文献[18],第25页。),[9]351它包括三类,即合同无效要件、合同可撤销可变更要件、合同效力待定要件。对此,均应由被告负证明责任。如主张合同无效的被告,应证明《合同法》第52条所列事项:1.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然而,学界多认为,《合同法》第44条所称“依法成立的合同”之“依法”,其所指乃《民法通则》第55条,并将后者规定之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套用于合同一般生效要件。[12]228通过“依法”转介的合同一般生效要件,是履行请求权之积极要件,属于权利产生规范的要件之一,应由原告对之承担证明责任。
问题在于,如果实在法既规定合同一般生效要件,又规定效力阻却要件,则由此导致的证明责任分配将又回到“谁主张,谁举证”的老路。即主张履行请求权者,须证明合同之一般生效要件(如不存在欺诈;《民法通则》第55条),而抗辩之被告须证明效力阻却要件(如存在欺诈;《合同法》第52条或第53条)。因此,为使证明责任分配得以明确,法规范仅可在积极之“一般生效要件”与消极之“效力阻却要件”中取其一。
(二)权利产生规范与权利阻碍规范之区分可能性:“一般与例外”的法政策
对于上述问题,实在法究竟应如何抉择?该问题涉及权利产生规范与权利阻碍规范之区分。不过,此区分在实体法上的可行性,是“规范说”经常遭受责难的软肋。对民法教义学(狭义之民法学)(拉伦茨认为狭义的法学与法教义学是同义语,参见本文参考文献[16],第72页。)而言,将法规范区分为权利产生规范和权利阻碍规范,实属陌生。这是因为,在实体法上,“某个事实应当被看作创设权利的事实或相反应被看作阻却权利的事实在结果上是无所谓的”。[13]270比如,意大利民法典注释书,以合同意思瑕疵之不存在(mancanza di un viziodella volontà)为例评注第2697条(举证责任)时,同样认为将“意思瑕疵之不存在”作为权利产生规范的要件事实(elemento cotitutivo)与将“意思瑕疵之存在”作为权利阻碍规范的要件事实(elemento impedi-tivo),在实体法上差别甚微。[14]92也就是说,法院最后支持以履行请求权为内容的诉求,我们既可认为该合同具备一般生效要件,也可认为该合同不存在效力阻却要件,二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并无差别。所以,将一般生效要件作为权利阻碍规范的要件,与将效力阻却要件作为权利阻碍规范的要件,对《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制度的设计,并无影响。
但这种规范类型的划分对实体法的(看似?)无关紧要性,针对的仅是法效果。就产生法效果之构成要件而言,其在诉讼中是否为案件事实所充分之证据审核过程,则攸关两造承担证明责任的范围。如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之善意,属于权利产生规范的要件事实,应由主张善意取得者承担证明责任;《德国民法典》第932条规定之“非善意”,属于权利阻碍规范的要件事实,应由反对适用善意取得者承担证明责任。[15]56-57虽然权利阻碍规范之要件,通常亦可将其“反面规定”(如非善意之于善意)作为权利产生规范的要件,但在这种取舍之间,其意义指向是法定之两造的证明责任分配。所以,“权利妨碍的事实的概念价值是足够大的,即使它只对证明责任的分配具有我们赋予它的意义”。[2]140
有些规范,直接就表明其属于权利产生规范还是权利阻碍规范。另一些规范,则须通过解释,才能被查明是权利产生规范或权利阻碍规范。[2]135依“规范说”,该项解释主要基于所谓“一般与例外”(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及下文所指的一般和例外,指的仅是实定法秩序形成的规则。参见本文参考文献[2],第131页。)的法政策。因为法秩序的形成,基于一般情况之通常规定与限制通常规定之例外规定的共同协力。根据此项法政策,权利形成规范与“一般情况”相连,它规定在一定前提条件(权利产生规范的构成要件)下,特定权利或法律关系应当产生。而权利阻碍规范则与“例外情况”相连,它表明若存在一个或数个要素(权利阻碍规范的构成要件),则该权利或法律关系例外地不产生。[2]129
(三)履行请求权产生之“一般情况”:证明责任分配对私法自治原则的具体化
根据法秩序中的“一般与例外”的法政策,法律规整或数个法律规整,均是以法律关系的“一般情况”作为法律规制的出发点,再以规定“例外情况”的权利阻碍规范作为限制。那么,何为履行请求权产生之“一般情况”?何为履行请求权不产生之“例外情况”?基于此一问题,判断合同一般生效要件是权利产生规范的要件,还是以效力阻却要件作为权利阻碍规范的要件,端视合同履行请求权产生之“一般情况”是否应具备一般生效要件。下文将以《合同法》文本中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为解释目标,阐明本已嵌入之证明责任意涵。
根据《合同法》第8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也即,合同成立一般即可产生相应的法效果,便有履行请求权的存在。因为立法者认为,合同成立时就已符合各一般生效要件(《合同法》第44条第1款),此即罗森贝克所谓的“一般情况”。或者说,此种规定系基于社会经验事实所作之立法政策上的推论,而非基于相反的推论,即成立之合同,多属效力欠缺者。此种立法上的考虑,还将在每项支持履行请求权的判决中得到体现。也就是说,即使《合同法》并无积极的一般生效要件,当判决支持合同请求权时,法官一定对一般生效要件作了积极的虚拟(此积极的虚拟,通过“操作规则”达成。普维庭在批评罗森贝克“不适用规范说”的基础上,认为应以“操作规则”解决事实争议不明时的法律适用问题。参见本文参考文献[4],第231页。)。
基于这种“一般情况”,(履行请求权)权利产生规范的要件仅包括成立要件,并无一般生效要件,主张履行请求权之原告,仅须证明合同成立要件便可(如果合同有附款或须批准登记,也应证明)。同时,立法者将效力阻却要件,作为权利不产生的“例外情况”,并以之为权利阻碍规范的要件,交由抗辩之被告承担证明责任。
此种将“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法》第44条第1款)作为“一般情况”之立法技术,其立法理由应植根于合同自由原则。该原则作为“法条形式的原则”,以私法自治这一“开放式原则”为基础。[16]353私法自治,作为一种受宪法保护的自由权,[11]30为保证行为之自由,准许各个主体根据他的意志自主形成法律关系,[17]142私法之功能并非指导或干预主体之行为,而仅是赋予主体之行为以某种法律效力。[18]21因此,基于私法自治,法律对当事人自治形成的合同,应作“有效性推断”(也有称作“有效推定”者(参见朱庆育:《意思表示解释理论———精神科学视域中的私法推理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洪学军:《民事行为有效推定规则的构造及其运用》,《法律科学》2006年第4期,第76页)。值得注意的是,在证明责任法上,推定有其特定含义,它是从法律规定之“前提事实”所作的逻辑推论。而此处对合同效力的推断,并无所谓法律明定之“前提事实”。因此,为全文概念之周延计,本文以“有效推断”称之,这不同于此处两个引文所指的“有效推定”。)。当然,私法自治亦有其自身“游戏规则”,其表现之一便是意思表示不得违反法律的强行性或禁止性规定等效力要件。
此点在证明责任分配中的逻辑贯彻就是,主张履行请求权者,仅需证明合同成立要件,此时若抗辩之被告未能证明效力阻却要件的存在,则合同在立法之“有效性推断”下,便发生当事人通过意思表示所追求的法效果。也就是合同效力要件,在私法自治的要求下,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所以,不是将一般生效要件作为权利产生规范的要件,而是将效力阻却要件的存在,作为履行请求权不产生的“例外情况”,此乃私法自治的具体要求。若非如此,则将打乱民法内部体系的统一,致使实体法上的同一行为在证明责任分配与该行为的要件构成体现之意思自主上,存有评价上的冲突。换言之,从整个私法以私法自治作为出发点的角度观察,证明责任制度实际上也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合理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自当符合私法自治的要求。
作为题外话但又值得说明的是,《合同法》为调和主体意思自治与国家管制之紧张关系,通过对合同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实则为效力阻却要件)设计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告诉我们区分合同(甚至可抽象至民事法律行为)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之意义,应主要是二者在证明责任分担上的不同,而非如拉伦茨所言仅具法学认识之意义。[19]429所谓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之区分,之所以能够体现私法自治与国家管制的分野,乃是通过对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规定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达成的。
至此,问题仍旧是应如何理解《合同法》第44条之“依法”以及其所转介之《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的一般生效要件?依本文所信,《合同法》第44条规定之“依法”,并非隐射《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之一般生效要件,而是指有关合同订立之形式要求(《合同法》第10、11条)、“要约、承诺”规则或其他订立合同的方式(《合同法》第13条以下)(也有将之称为合同订立的义务性规定(参见洪学军:《民事行为有效推定规则的构造及其运用》,《法律科学》2006年第4期,第78页)。但本文以为,称义务性规定,令人费解,合同的形式要求以及要约、承诺规则,均是合同成立的必备条件,前者是合意的外部表现形式,而后者则是判断是否存在合意的规准。)。此等合同形式、订立的规则或方式,均属于合同成立的范畴,应由主张履行请求权之原告承担证明责任,自不待言。并且,《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之一般生效要件,“属于抽象性、原则性规定,其主要功能不是作为裁判规则的功能,而是作为指导性规则的功能,目的在于告诫民事主体在实施民事行为时应注意的问题”。[20]156而客观证明责任,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活动毫无关系,其针对的是真伪不明,并以此保证法官裁判义务的实现,[4]26其规范属性应为裁判规则。所以,将《民法通则》第55条这种行为规范引入证明责任的探讨,显然不合时宜———导致一般生效要件在证明责任安排上的混乱,已如前述。
在排除《民法通则》第55条对合同效力要件之证明责任安排上的搅扰后,还须注意《合同法》第9条。该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此处从正面将“具有行为能力”规定为一般生效要件,似乎违反了本文如上关于效力要件的证明责任分析,即行为能力要件,应仅作为效力阻却要件(能力欠缺者订立之合同,无效或效力待定)。不过,此条规定之“具有行为能力”,处在《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中,而非规定于《合同法》第三章“合同的效力”中。依体系解释而言,该条并非是一项体现国家管制之效力要件的规定,而是如《民法通则》第55条一样,是立法者倡导的一种行为规范,仅具指导意义,非属裁判规则之列。所以,就合同效力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的探讨而言,也可忽略此条的干扰(不同的观点,可参见本文参考文献[3],第554页。)。
因此,《合同法》并未将“合同一般生效要件”(权利产生规范的要件)作为规范对象,而仅规定了“效力阻却要件”三种类型(权利阻碍规范的要件)。[2]285虽然本文未逐一“陈列”外邦立法例以获取某种普适性知识,却不忘申明《合同法》在效力要件上的证明责任安排,有其比较法根基,即多数立法例均以效力阻却要件为规范对象(立法例中仅《法国民法典》从积极方面规定了契约的有效要件,此与其立法背景有关。对此可参见洪学军:《民事行为有效推定规则的构造及其运用》,《法律科学》2006年第4期,第79页。)。当然,在法国法系,合同要件还包括“原因”,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343-1345条的规定。在证明责任分配上也采用罗森贝克的“规范说”的前提下,[14]85意大利最新学说汇纂认为,原因要件也应作为合同效力阻却要件之一类,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21]292
《合同法》的立法者不自觉(还是自觉?)地遵循了“规范说”在合同效力要件上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这是值得庆幸的,因为不会有精通证明责任者,甚至也不会有仅凭法感之门外汉,要求原告证明意思和表示的一致、虚伪表示的不存在、内心保留的缺乏、欺诈或胁迫的不存在等。此外,由于诉讼过程中,主张责任的标的和范围与证明责任相一致,[22]856原告也无须主张(或陈述)合同符合各项一般生效要件。否则,在每件合同纠纷中,令原告陈述自己具有行为能力———本人于立约时已成年并神志清醒,不免荒唐。
四、《证据规定》第5条之适用:对隐藏漏洞的补充
依上文的分析,由于一般生效要件并非(履行请求权)权利产生规范的要件,原告对此不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就生效要件而言,原告应证明者,仅限于特别生效要件。但根据《证据规定》第5条,主张履行请求权的原告,应承担合同生效要件的证明责任。该条所称之“生效要件”,若纯就文义解释,其所指,应既包括一般生效要件又包括特别生效要件,断无可能将之限缩解释(为获得更“忠于法律”之印象,司法裁判或学术研究上,多将目的性限缩仍自称为限缩解释。参见本文参考文献[16],第267页。本文所论,显已超越文义,非限缩解释的范围,而需以目的性限缩的方式为漏洞补充。)为“特别生效要件”。
因此,《证据规定》第5条未考虑到一般生效要件在证明责任分配上的特殊性,将之与特别生效要件作同一规定,出现所谓“隐藏的漏洞”(值得注意的是,《证据规定》第5条第1款的问题还在于,该条款后句规定主张撤销者,须证明撤销事由,也就是应证明者为效力阻却要件。所以,就此点而言,该条款前后句自相矛盾。)。[16]254之所以称为“隐藏的漏洞”,在于《证据规定》第5条并不欠缺对一般生效要件可资适用的规则,惟依规范目的,该条并不适用于一般生效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隐藏漏洞的产生,原因在于规整出现目的限缩式价值判断矛盾,[23]318-319即《证据规定》第5条之规定过于笼统,其适用范围过宽,依规范目的应限缩其适用范围而未限缩,则产生此价值判断矛盾。
对于隐藏漏洞的填补,一般借用目的性限缩方法。与类推适用相反,目的性限缩的正义命令是,不同事件应作不同处理。[16]268既然一般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不同于特别生效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则应依目的性限缩方法创设一限制性规定,将《证据规定》第5条所称“生效要件”限定为“特别生效要件”。
通过目的性限缩方法创制的限制性规定,便可填补《证据规定》第5条存在之隐藏漏洞。但被该限制性规定排除适用《证据规定》第5条之一般生效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至少在《证据规定》上———便缺少可供适用的规则,这是否又构成另一法律漏洞?
既然《证据规定》第2条已肯定“规范说”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并且前文依据此原则,就可依解释得出《合同法》关于“一般生效要件”的证明责任安排,即“一般生效要件”并非《合同法》的规范对象,需要证明的是一般生效要件的对立面———效力阻却要件。所以,纵使《证据规定》第5条第1款前句未规定“一般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仍无漏洞可言。甚至,没有《证据规定》第5条之规定,亦可通过对《合同法》相关条文的解释,得出合同纠纷案件中二者之证明责任分配。
五、余论:民法解释论之发展向度
虽然《证据规定》第2条依循“规范说”确立了我国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但异议者从未停止对权利产生规范与权利阻碍规范之区分的批评,认为其在实体法上无以区分或难以区分。但恰如“规范说”的创始人罗森贝克所言,惟有在对实体法的理解中,我们才能辨明某一规范是属于权利产生规范还是权利阻碍规范。
所以,与其对实在法之批评姿态的“坐而论道”,不如详究其适用之途。如本文所论,针对履行请求权,其权利产生规范之要件仅包括合同成立(有时还包括特别生效要件)。而《合同法》规定之效力阻却要件,则为权利阻碍规范之要件。在这种基于《合同法》文本并以证明责任为目标的法解释后,便可得出二者各自的证明责任负担。由此也表明,中国民法学在立法论大旗下,大致建立起完备的私法体系,但立法的建构理性毕竟有限,学界遂不断有学者提出中国民法知识形态应转向解释论的路径。[24]不同于立法论之政策性论证,民法解释论以实在法为依托,研究法适用中的具体问题,其最重要的任务乃是阐明个别法规范、规整之间,及其与法秩序主导原则间的意义脉络。因为法律文本中,法规范并非彼此无关地平行并存,而是以各种意义脉络相互关联。[16]317对“规范说”而言,证明责任的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因此,民法教义学似不应忽视已嵌入实体法之证明责任内容,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解释论亦不排除价值判断,毋宁是与立法论一样也包含价值判断,只是此两种价值判断迥然有别。[25]340就本文所论合同生效要件而言,它通过合同(法律行为)这一规定功能的概念[16]355,指向私法之基本原则———私法自治,再以其证明责任分配具体化该原则。所以在价值判断上,合同效力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与整体之私法精神相一致。在这种解释论进路上,我们不仅要求法教义学为裁判提供可堪适用的法规范(请求权基础检索的技术),[26]168还苛求教义学语句为二者指明证明责任负担。就此,借用实体法中的证明责任规则,我们还可改造民法实例研习之“请求权方法”,[1]42将该方法中请求权基础和“抗辩基础”(既然在“请求权方法”中,请求权与抗辩之关系是该方法之基本思维模式(参见本文参考文献[1],第175页),则与请求权基础相对者,自然便是“抗辩基础”。因此,本文生造“抗辩基础”一词,意在表明此处所称“抗辩”非所谓诉讼上的抗辩,它指涉着“规范说”中的相对规范(权利阻碍规范和权利消灭规范)。),与“规范说”之规范分类方式———基础规范和相对规范予以对接。如此,基于“请求权方法”之实例研习,方可透视裁判之全过程。
本文标签:四川自考 法学类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http://www.sczk.sc.cn)
⊙小编提示:添加【四川自考网】招生老师微信,即可了解2023年四川自考政策资讯、自考报名入口、准考证打印入口、成绩查询时间以及领取历年真题资料、个人专属备考方案等相关信息!

(添加“四川自考网”招生老师微信,在线咨询报名报考等相关问题)
填写下方信息,马上领取四川自考《备考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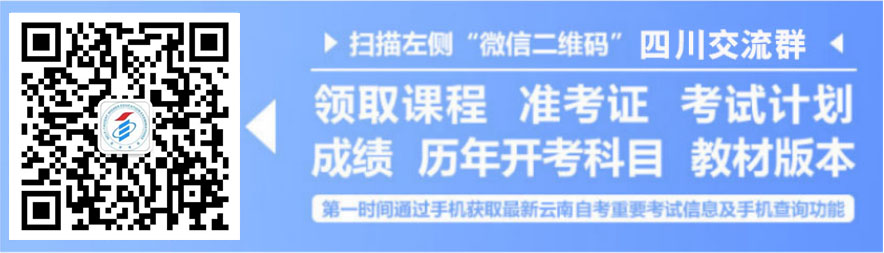
《四川自考网》免责声明:
(一)由于考试政策等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本网站所提供的考试信息仅供参考,请以省考试院及院校官方发布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
(二)本站文章内容信息来源出处标注为其他平台的稿件均为转载稿,免费转载出于非商业性学习目的,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您对内容、版权等问题存在异议请与本站联系,我们会及时进行处理解决。联系邮箱:812379481@qq.com
 ×
×














